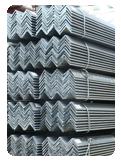暮色漫過荒園時,我又摸到了那串生銹的鐵絲門環。葡萄藤的卷須早把鐵門織成了綠網,風過時葉隙漏下的光斑,像極了外婆縫在我童年襯衫上的月光紐扣。那年她教我辨認雌雄花,指尖沾著葡萄蜜的清香,說雄花會落盡,雌花才能結出飽滿的穗子,就像人生總要舍去些什么,才能將珍貴的東西釀成甜。
如今藤蔓攀到了老屋屋頂,當年我踮腳摘葡萄的磚垛已塌成半堵矮墻。井臺邊的鵝卵石還留著被井水浸過的涼意,只是角落淤滿了敗葉,再沒有赤腳踩過的咯吱聲。記得有年盛夏暴雨,外婆把我裹在藍布衫里躲在屋檐下,雨珠順著發髻往下滴,在地面上砸出銅錢大的濕痕。她從瓦罐里摸出一把葡萄干,在我掌心堆成小山:“嘗嘗,這是去年的‘小陽光’,曬干了還留著夏天的味道。”那些皺巴巴的果粒在舌間化開時,我看見她鬢角的白發上掛著水珠,像葡萄藤上未晞的晨露。
后來,外婆走了,葡萄藤卻瘋長著,仿佛要把她的故事都藏進年輪里。如今我蹲在荒草叢生的井臺邊,伸手去夠藤蔓上掛著的野葡萄,果實只有指甲蓋大,酸澀得讓人皺眉。可咬破的瞬間,記憶卻洶涌而來,外婆晾葡萄干的木架,陽光將紫果曬成琥珀色,風一吹,像一串風鈴叮當作響。她教我用棉線把葡萄干串成項鏈,說戴上這個,整個冬天都能聞到夏天的香味。可那時的我總在半夜偷偷吃掉項鏈,第二天清晨,外婆看見散落的棉線,只是笑著往我兜里塞新的:“小饞貓,明年夏天給你種個更大的葡萄園。”
夜風掀起藤蔓的葉子,恍惚間又聽見草棚里的窸窣聲。外婆總在睡前講葡萄精的故事,說藤蔓最密的地方住著個穿綠裙子的姑娘,會把最甜的那顆葡萄留給守園的孩子。我常在她的故事里睡著,醒來時,手腕上套著葡萄枝編的手環,枝丫間還沾著新鮮的樹液,像綠色的眼淚。如今老屋早已塌成土堆,只有幾束干枯的葦席插在泥里,風一吹就發出細碎的嗚咽,像是誰在輕輕哼著那年的搖籃曲。
離開荒園時,我摘了片最完整的葡萄葉。葉脈在月光下泛著銀白,像外婆老年斑密布的手背。當年她牽著我走過藤架時,總讓我踩著她的影子走,說這樣就不會被曬到。現在我的影子長長地投在地上,卻再也找不到另一道影子來重疊。路過村口的雜貨鋪,看見玻璃罐里裝著進口的葡萄干,包裝上印著鮮亮的紫葡萄,可我知道,再也沒有哪顆果實,能像外婆掌心的那顆一樣,裹著井水的涼、草棚的蔭,和整個夏天的星光。
藤蔓還在往舊墻的裂縫里鉆,像極了那些怎么也止不住的思念。我把葡萄葉夾進日記本,葉尖的露珠落在紙頁上,暈開的水痕漸漸變成紫色,就像那年外婆替我擦葡萄時,指尖染上的果漬。原來有些味道永遠不會消失,它們藏在藤蔓的年輪里,藏在井水的倒影里,藏在每個被月光泡軟的夏夜,等著風一吹,便從記憶的深處簌簌落下,鋪滿一地。(龍鋼公司 吉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