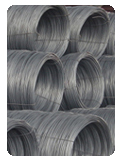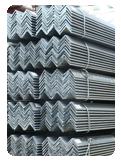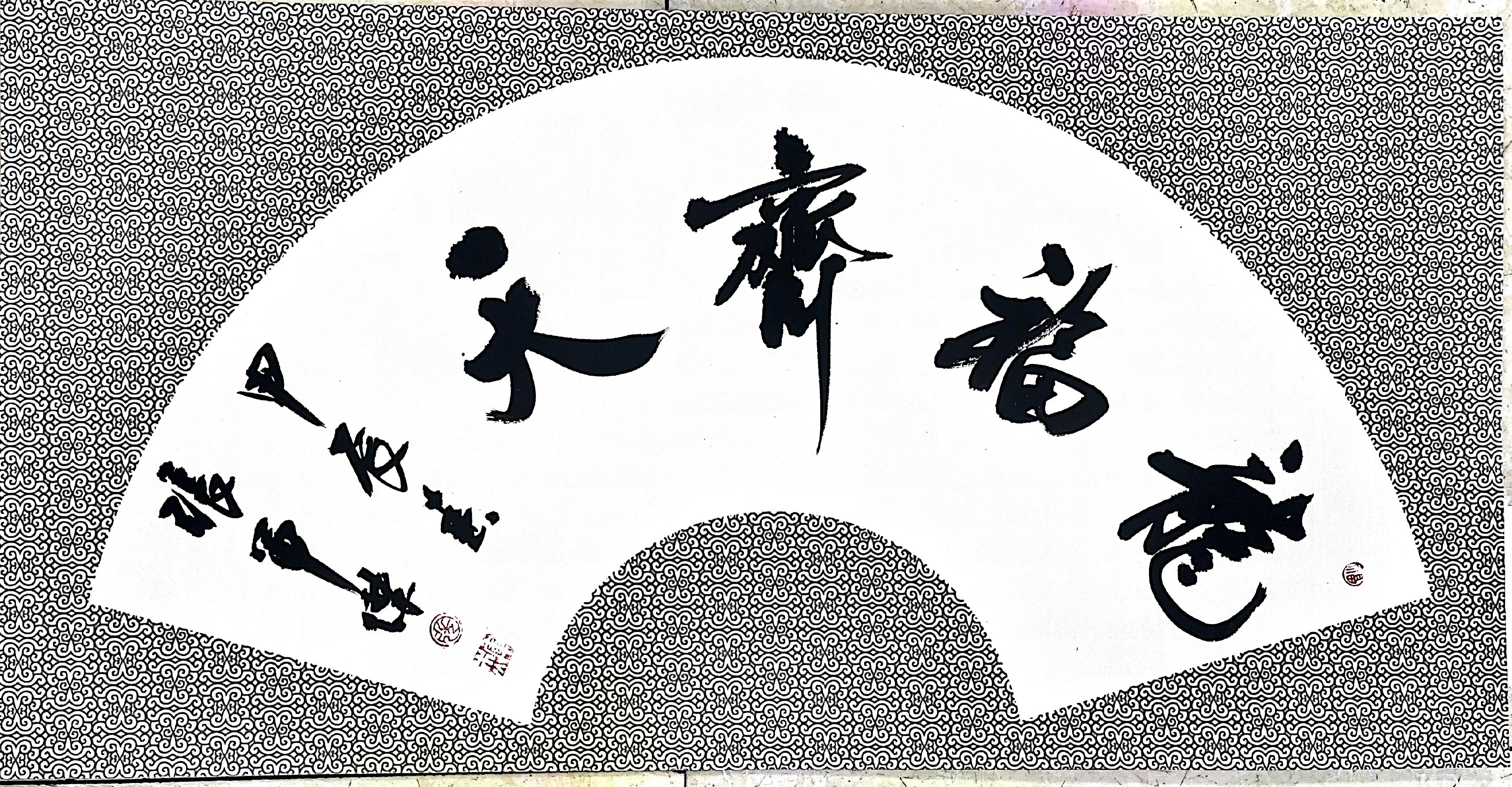瓦藍的天空不留一絲白云,太陽下的熱火青年,在黃土高坡上光著膀子從山的這頭跑到了那頭。輕風如江南水鄉女子般溫柔的手,輕拂著山梁上的一排排白楊。一座連著一座算不得偉俊的山,悄悄圍成母親溫暖的懷抱,城隍梁這個小村莊貪婪地臥在山間。在村莊里田間地頭踱步,那歪脖子杏樹、山丹丹花、腦畔的棗樹、潔白的羊群盡收眼底,悄然間織成腦海里最初的風景。
夏日熱浪肆無忌憚地襲來,蟲叫鳥鳴匯成的樂章讓早已毫無生機的黃土地更增添了一份靈動。在粟米地里,父親和母親拿著鋤頭,揮動著有力的臂膀,一鋤頭又一鋤頭,把地里成簇的粟苗和雜草一點點鋤去,回首望去,原本有些雜亂的粟地變得井然有序。歇口氣的工夫,父親摘下破舊的草帽,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拭著額頭的汗水,握著鋤頭的手粗糙得與地畔上那棵歪脖子杏樹皮一般無二,黑黝黝的臉像被抹了一層山腳下老溝垢到發黑的淤泥,矮小卻不失健碩的身子,像一根堅實的木樁,緊緊釘在莊稼地里,仿佛不知曉夏日的燥熱。直起腰的父親扯著嗓子喊:“二娃子,把煙袋給我拿過來。”和哥哥在歪脖子杏樹下玩耍的我,抄起父親的旱煙口袋,飛奔著送到父親手里。接過旱煙口袋的父親,用煙鍋挖幾下煙絲,用銹黃的大拇指按幾下,順手用火柴點上,蹲下身子,猛吸幾口,瞬間把疲勞卸去了大半。
怕曬的我忙著跑回歪脖子杏樹下,繼續和哥哥玩起了蕩秋千。無論春耕秋收,只要父親和母親在地里忙活,這歪脖子杏樹下就是我和哥哥的游樂場。父親和母親鋤地時,我和哥哥用父親背驢草的繩子綁在樹杈上,撿一根粗壯些的木頭套上去,就做成了簡易的秋千,我坐在上面時哥哥推,哥哥坐上面時換作我推,玩得不亦樂乎。玩膩時,便讓哥哥爬上杏樹,給我摘幾顆還未成熟的杏子,當我齜牙咧嘴地啃著滿是酸澀的杏子時,鋤地的母親笑著說:“現在的杏兒酸得吃不了,你們兩個要是沒事干,去捋一些澤蒙花,也可以刨幾株山丹丹花。”母親是喜歡山丹丹花的,每年夏天,總要挖幾株回來,摘進菜園子里。
在母親的指引下,我和哥哥在粟米地的背洼上輕松找到了幾株盛開的山丹丹花。六片卷曲的花瓣紅得仿佛在滴血,淡黃色花柱上的六個花蕊,變成了羞紅了臉的少女。我和哥哥用手小心翼翼挖著花根部的泥土,生怕折斷了花枝,若是斷了花枝,這山丹丹花即使栽進了母親的菜園,也是活不了的。山丹丹花在陜北的土地上算不得稀罕物,但每一個陜北人都甚是鐘愛。一株山丹丹花通常能開出一朵花,開出三朵花的甚是少見。母親曾經栽種過開五朵花的山丹丹花,是父親在溝旮旯割草時挖回來的,母親一直小心看護。我和哥哥偷摘大伯母家的棗時,也是繞著這株山丹丹花走。
栽著山丹丹花的地畔下是大伯母家的幾棵棗樹,是我和哥哥經常“光顧”的地方。大伯母是村里最慈祥的老人,看到我和哥哥摘了還未變紅的棗兒,從不會攆來,也不會告訴母親,應該是怕我們慌忙逃跑中從樹上摔下來。我清楚地記得,每年秋天棗兒成熟時,大伯母會端著滿滿一篩子新鮮的棗兒,送到我家里,說是給我和哥哥解解饞。那時,父親和母親為了防止我和哥哥“禍害”大伯母家棗兒,便在鋤地時帶上我和哥哥,讓我們在地畔那棵歪脖子杏樹下玩。
烈日當頭時,趁著休息的間隙,母親會去把吃草的驢重新拴個地方,父親也坐到了杏樹下,叼著煙鍋子,望著對面山坡上好似一團團棉花的羊群,輕聲道:“過兩年有錢了,咱也買一群羊。”他仿佛是在自言自語,但我知道,從那時起,他心中已經做好了扛著攔羊鏟子,趕著潔白的羊群在山坡上吃草的打算了。直到多年后,父親終于實現了他最初的愿望,農忙之余,趕著羊群到山峁溝洼草木豐盛的地方,讓羊盡情地咀嚼草木春芽。
日月如梭,從長大后我逐漸遠離了城隍梁這個小村莊。那片熱土上,歪脖子杏樹依舊年年茂盛,只是樹下沒有了秋千,棗樹只剩一棵,每年還能結出些棗兒,菜園里的山丹丹花早就沒了蹤影,只有父親還是早出晚歸攔羊。我的腦海里,留存的最多的還是春的杏花,夏的山丹丹花,秋的果香和冬的銀裝素裹。夜深時,我常把一片又一片的記憶畫面,無聲中寫成了一首朗朗上口的詩,凝練成了一段美妙的音樂,最終演繹成故鄉的原風景。(漢鋼公司 薛生旭)